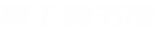白天的阳光里,我穿着毛衣,站在院子里看火越烧越近。烟升得很高,蔓延成十几堆火。“还是没有得救!”我说。夏一米看了看,说:“以后再按铃!它要燃烧了。”Baloma一直都很冷静。她说她家没有森林,烧荒不是她的事。“村里到处都是树——”我不敢吓唬她,但我怕火会烧了房子。
黄昏的光线在暮色中冲了出来,村下的钟声刚刚急促地敲响。空在空中,灰尘飘下了整个天空,我们退到了房子里。关上门窗,离开前安顿好Baloma。
跑到村口的时候,看到的男人都老了,只有一米和神父是中年人。夏一米的膝盖是两年前割的。里面有钢钉,她很胖。去那里没用。看那些肩上扛着铲子和锄头的人。我认为这些工具太弱了,无法应对火灾。就算是要阻拦,也只有二十几个人。我被烟呛住了,跑回去看Baloma,他一个人锁了卧室的门,躺在床上。“你看过南和西撒哈拉吗?”我问她。“不!我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了!”Baloma开始摸她的羊毛披肩,急于挣扎。
“我换球鞋,你留着,我跑——”我脱下靴子喊了一声,“关上门,小心浑水摸鱼。”然后跑了。
还看到直升机转弯,邻山的人三三两两低头往火场跑。寒冷的夜晚,找不到神父和夏一米,大火烧到了泥路上的小桥。
我跑到高速公路上,拼命地喘着气,却看到有一台像开山机一样的大机器压着森林,大约有200人以各种方式看到了消防车道。那些人的身边,不时掉落一团燃烧的小火。火光中,每个人都排着黑纸,一个个摇着。
“西南——”我放开喉咙,对着人群喊道。烟太重,有些人受不了呛。锯了一次树后,他们冲到路上呼吸。
恨这些人的无知,真是刻不容缓。孩子们呢?孩子们在哪里?“南——”我又喊了一声,不敢走进火林。
一个不认识的人给了我一根大棒,说:“你把路守在这里,如果有小火飞过,就上去扑灭。”一直有树枝着火。顶上的那些够不着,没时间来个路边小火。女人在这里,我们在这里,男人深入那边的火林。“西-萨——”我一边工作一边喊,但没有回音。火,带着可怕的声音,慌慌张张地吞了下去。
“林务局死了!怎么可能只有普通人救!”我大喊
“为什么不行,十几个都在一起烧,他们来不及了!”
边骂边生火,等到最激烈的地方被人故意反方向放火,火巷烧过去就被隔离了。
深夜,村里的妇女们在他们烧焦的树林前放声大哭。想到Baloma一个人在家,她丢了拐杖,慢慢地往回走。
夏一米也回来了,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,孩子还没到家。
“如果孩子出事了,我就活不下去了。”Baloma也不哭,就这样。两张黑脸刚进门。我上去,抓住它,打它。我的头和身体都被打了。在这之后,我追了它,又打了它。孩子不反抗,抱着头蹲着。那天晚上,因为担心余火重燃,大家都不敢睡觉。阁楼上的楠悄悄问我:“Echo,你什么时候走?”我说几天。他补充道:“如果Baloma死了,你会带我和塞萨尔去台湾省吗?”我跑过去,用毯子把他抱在怀里,下巴抵着他的头,什么也没说。旁边睡着的塞萨尔闻到了烟味。
“接起来很开心。送人很无聊。我会坐火车。”我说。
巴洛玛没有说话。她那天没说话。她摸了摸沙漠毯子,让我把它拿走。我又写了生日,说平日不沟通。当我回到中国时,我必须用西班牙语写它。
据说每个人都应该睡觉。早上,只有我和夏一米去小镇的车站赶去马德里的火车。然后飞到瑞士,回到台湾省。
那天晚上,我没有睡觉。孩子们的衣服和裤子修好了,厨房悄悄打扫了,浴室又轻轻擦了一遍。回房间数一下旅行支票。除了一百美元,其他的都签了名,封在信封里。这一切,楠看着我在灯下做,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我们不说话。在早上6点20分的火车上,孩子们出门时正在睡觉。夏一米接过箱子,装上车,巴洛玛爬进了院子。我跑过去帮她,摸摸她的脸,说:“亲爱的,别担心,放心等。上帝不会让人饿死的。”她点点头,微微颤抖着,穿着一件长袍。我吻了她,问她早上能不能看到山林,她说不能。
推荐阅读
- 好的爱情是天堂,坏的爱情是地狱
- 90后结婚后,比婚前更孤独
- 子夜荐读 | 运动,是治愈一切的良药
- 三毛流浪记主演 《三毛流浪记》的扮演者已长大 曾因头部受伤息影7年 至今单身
- 子夜荐读 | 纠结无用,不如让心思简单些
- 子夜荐读 | 为何生活总是这样
- 子夜荐读 | 有一种自律,叫熟不逾矩
- 子夜荐读 | 人到中年,要学会给自己看“病”
- 子夜荐读 | 人生如镜,镜透百态
- 武汉市漫画研究会新任掌门人蒋勇呼吁:“三毛式的传统漫画急需复兴”